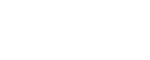寒暑假的意义就是为了避免像我这样的学生在学校待久了,容易得自闭。
而上学的意义也是为了避免像我这样的孩子在家里待久了,容易犯神经。
考虑到像我这部分学生的存在,学校为了维持两极平衡,在我们快要自闭的时候适时的安排假期放我们回家休息,在我们快要神经的时候召回我们返校学习。
在自闭与神经之间摇摆不定,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病态平衡,最后学校会在学生即将崩溃的时候告知我们“病人情况很不稳定,需要转院治疗”,于是我们就毕业啦,于是考研的考研,工作的工作,各有各的去处了。这病,也就交给了上一级大学或社会再去治。
其实也没必要去治,久病成良医。一部分像我一样的学生早就学会了在快要自闭的边缘时,从“神经”处借一点快乐和乐观,学会了在快要神经的边缘时,从“自闭”处挪一些冷静和静思。在乐观与冷静中做好摆在手边的事情。
唯一的不同可能是:高中的时候,我觉得摆在我手边的事情分为两种:可做可不做的与不得不做的,看起来很单纯,做起来也的确很简单。而上了大学以后,可做可不做的事成了不得不做的,不得不做的又成了可做可不做的事。于是我又发觉事情忽然变得微妙起来,我所熟悉的关于事情的两种分类结合成了一类: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的事。这事看起来很矛盾,其实做起来比看上去还要矛盾。
但也相安无事,我偶尔也会怀念我的高中生活,怀念我的同学和老师,他们让我拥有了一段快乐的回忆,在回忆里我是一个十足的神经病,可以说“神经”有余,但不够“自闭”。我也不排斥我的大学生活,不排斥我的室友和导员,我能确定在未来的回忆里我同样也会怀念他们,因为他们让我变异出一种可以在“自闭”与“神经”之间切换的超能力,带着这股超能力让我可以去处理那些看似矛盾的“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之事”,兼之“神经”与“自闭”。
“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”我把其中的“誉与非”理解为“神经与自闭”,其中的“劝与沮”则对应为“乐观与悲观”。而我之所谓大学教育,就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一部分学生能在“誉与非”之间找寻一个平衡点,在“劝与沮”之中调节好自己的心态。在经历一件件可做可不做的不得不做的事情过后,定乎内外之分,辩乎荣辱之境,斯已矣。
版权声明
本站文章收集于互联网,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,文章仅供学习观摩,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如有侵权请联系邮箱tuxing@rediffmail.com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wuliandi.com/gaozhong/gszw/3663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