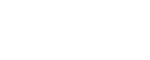冬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:从阴暗天空,一朵云再也忍不住了,哇的一声,将所有伤心哭出来,从云端洒下,洒到山麓,从山麓洒到繁茂的村庄,洒入小孩嫩红的手掌,洒入冻得坚硬的冻土上——硬如一块工地上的砖头的冻土。
那样坚决,那样随意,却又那样强硬不管。一场雪,可以召出一城小朋友;一阵风吹,伤害了一排小树;一场冰雹,树木就碰得粉身碎骨,依旧顽强生长。反正冬天这样任性,不理性。
冬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:落叶从天空纷纷划落,划成一条优美的曲线。有些动物开始找洞穴或者大吃大喝,准备进入冬眠。然后,忽然有一天,大雪把所有道路都占领了,北风把所有上空封锁了。冬天犹如所向披靡的将军,攻无不克,战无不胜。
而关于冬天的名字,必然曾经有一段神话:在《离骚》之前,在《史记》之前,在女娲补天之前,浣纱人手在溪水中感到的冰凉,羊吃小草忽然乏味、干枯,动物忽然消失……它们决定用一种惊讶的口型来为这季节命名——“冬”。
现在冬爷爷的来到,让世间成了雪花的主场,有负责管天地间的高度,或管土地的重量,还有些管肥沃度。可是雪花还太小,比较羞涩,不敢轻易说出结果,怕被人关注。
还有些停不下来的雪花,负责数枯树有几棵,树苗有几棵,老树有几棵,共有几棵树。把每一年数据编成一册书。
冬天必然曾经是这样,或者在遥远的地方,它也还是这样。
版权声明
本站文章收集于互联网,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,文章仅供学习观摩,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如有侵权请联系邮箱tuxing@rediffmail.com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wuliandi.com/chuzhong/cyzw/27713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