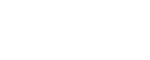金秋九月之际,我的嘴有些馋了,看着李阿姨买来的海棠果和板栗,我饱够了眼福,却没有想吃的欲望。李阿姨也不恼,反而笑着打趣道:“小丫头片子,嘴还挺叼。”我笑笑,不可置否。但却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直到在电话中偶然听爸爸提起:“茶季到了,山上的大麦莓也该青了吧!”我才恍然大悟,忙问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摘。爸爸详装怒道:“就知道要吃的,不要爸爸了,哎呀,我好伤心哦。”听得我咯咯直笑。
小时候,每当这个季节,爸爸就会带我去茶山,把我架在他的肩上,笑嘻嘻的开玩笑:“山大王家的小妹妹来巡逻喽!闲人退避!”而妈妈则在一旁数落爸爸没个正经,却自己采了山花编成环戴在我的头上。
有时,我坐在地上,看见土地里爬出了蜘蛛小虫,便吓得哇哇大哭,结果我刚一张嘴,便有几颗酸甜可口的小玩意儿堵住了我的嘴。我想吐出来看看是什么,却又有些舍不得。我纠结的小表情逗乐了妈妈和爸爸。爸爸朗声大笑:“哈哈,好吃吧!走,我带你去找,我们比比谁找的大麦莓多!”于是,我便得知了它的名字叫大麦莓。我却天真的以为它只是单纯的与大麦长得像,所以叫做大麦莓。
我在爸爸的肩上幻想着那金灿灿的美味,不知不觉流出了口水,爸爸无奈道:“我的小祖宗,幸亏到的早,不然还不被你的口水淹没了!”我脸一红,强行插入话题:“在哪呢,在哪呢?”爸爸用手指了指几枝带刺儿的枝丫,我看到了几簇红澄澄,亮晶晶的小精灵。我走近了它们,摘了一颗在手上把玩。突然有些不舍得吃它们。爸爸好似看出了我的纠结大大咧咧的两手一摆道:“你不吃它们它们也会落的,它们生命的价值就没有啦!”我一听,好似是为我的罪恶感找到了理由,光明正大的吃了起来。
自打那以后,每次爸爸妈妈上山,回来都会给我带上一篮大麦莓,渐渐地,就养成了习惯。即使他们外出,每年也不会忘,对我来说,这是一种特殊的关怀。
可前年,村门口来了一群收药材的人,他们用方言和村民交谈,大概是说什么覆盆子要青的,价钱好商量之类的,我却从未往心里去。直到我在五叔家,看见一筐青的大麦莓,我才知道,覆盆子就是大麦莓。我的心无力地抽痛,那给我温暖的大麦莓,它们正安静地躺在那儿,作为不知名的、没有感情的商品,将被出售!我试图阻止,但是就像叔叔说的:“你能叫我别摘,你有能止得住那些村民吗?”是啊,我阻止不了,我自嘲:我能做什么呢,能做的也只是和叔叔拌两句嘴而已。
灰蒙蒙的天下起了雨,滴落到我的脸上,咸咸的,分不清是雨还是泪,我踏着泥泞的小路,再次来到茶山。这里嫩绿的茶尖已经冒出来了,给人以生命的气息。几道凉风吹过,我清醒了几分,继续往前走。潮湿的泥土,弄脏了我的鞋,枝丫上的雨水沾染了我的雨衣。形成一颗颗坠落的流星。但我却无暇管这些,终于我来到了大麦莓的枝丫边。光秃秃的,就像我的心,凉透了。
“覆盆子以八、九月熟,故谓之割田簏。覆盆子以四、五月熟,故谓之插田簏,正与别录五月采相合。二簏熟时色皆乌赤,故能补肾。其四五月熟而色红者,乃蓐田簏也,不入药用,陈氏所谓茅莓当覆盆者也,盖指此也。”如今我长大了,当我看见这一段关于覆盆子的介绍时,我才发现我是自私的,回忆藏在心里又何尝不是好事?我期待着今年茶季的再次相见。再见了大麦莓,再见了我自私可笑而又温暖的童年。
版权声明
本站文章收集于互联网,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,文章仅供学习观摩,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如有侵权请联系邮箱tuxing@rediffmail.com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wuliandi.com/chuzhong/cszw/27903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