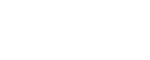在小镇的大街小巷还未贴满红底黑字的宣传告示时,老龙和三轮车早已教会了人们垃圾分类。
吱呀作响的旧三轮,载着一个矍铄老头,人唤老龙,或许他本姓不是“龙”,只是人们见他耳背,叫顺了。
“收废品——”冗长,又回转,尾音故意拖得长,经了风霜的沙哑嗓子,和着晨露和微风,吹进每个人的耳朵,一嗓过后,小镇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。
留存大大小小的纸盒,铺平一天一天的报纸,成果是或多或少的硬币。举手便能化腐朽为所需,依劳动取所得,自立又环保,纸盒子与空瓶子往往能决定童年糖果的数量。
老龙的吆喝又响起了。孩子们从玩耍的聚集中散开,各自奔向自家的院落,复又聚拢,身后拖着个大纸箱,与小小身形相称,俏皮又滑稽,“有废品呀——过来收哟——”舞动双臂,扯着嗓子叫住旧三轮,往往一声还不够,要两声,声音似线,拉着快要远走的三轮。
三轮车的刹车松了,停下来,会“吱”一声。耳朵背的人会把声音故意抬得高,“慢点儿,一个个来。”老龙的提醒也比常人分量重,孩子们乖巧地站成一列,年幼的我在队中骄傲又兴奋,努力地将脖子上仰,老龙正对着我笑,酱色的脸似被雕刻,阳光照及每一寸坎坷,盘根似的枯瘦手接过,折叠成细长状,置于杆秤间,动作徐缓,秤砣的位置一点点地向秤梢挪,平衡时,徐徐吐了口气,复又弯腰,拎起另一个,虔诚得像手执天平的正义之神。而空瓶子向来就是你说几个便是几个,连着编织袋一齐扔进旧三轮,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,老龙深信。
路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只墨绿铁箱。白色油漆刷着“旧衣回收”,四字方正得很,孤零零地杵在那儿,行人匆匆,绿皮箱也极少得到关注。一天,老龙路过,停车驻足,仔细研究,目不识丁的他拽住一位学生,急切地想知道意思,“哦,收旧衣的。”学生与他比划了半天,老龙才明白。想来那时也是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一两年,时值隆冬,遥想蜀地应更寒,老龙便号召人们拾掇孩子小的、些许时候不穿不用的衣服,塞进绿皮箱里,大抵是他平素待人和善,不诈不欺,人们也都愿拨拉出些时间,整理,洗净,曝干,叠齐整了,郑重地放进绿皮箱,绿皮箱渐渐由空变满。那年,老龙一直套着洗得发白的灰外套,终是没见那件轻易不常穿的黑棉袄,应该是捐了吧。
后来,我们渐渐长大,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,常有吃不完的食物过期了,老龙心疼地看着粮食被糟蹋,骂声“作孽”,夕日欲颓之时,翻捡垃圾箱,撕开包装,掰碎,撒在草地上,犒劳了地上的小虫和天上的飞鸟,来回往复,人们也争着效仿。老人们把坏了的豆制品碾碎,埋在树周围,滋润了一方土地,楼下的枇杷分外甜,柿子也照眼红。果实流光之时,不忘加一句“老龙教的!”
日子一天天过去,老龙更聋了,灰黑的发早已被风吹白,小镇也从曾经的寡淡苍白变得流光溢彩,曾几何时,老龙臂弯上多了个红袖章,认真地琢磨起垃圾分类,“废电池过期药不能乱扔·····”童叟皆识。
即使此去经年,老龙也依旧一如既往。
版权声明
本站文章收集于互联网,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,文章仅供学习观摩,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如有侵权请联系邮箱tuxing@rediffmail.com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本文地址:https://www.wuliandi.com/chuzhong/cszw/274918.html